Robotaxi,正迅速从一个“未来设想”,转变为一个“当下进程”。
近几个月,这一进程在全球两端同时提速:
在美国,作为行业先行者的Waymo,正迅速拓展其商业布局。
在旧金山、菲尼克斯等“沙盒”城市成功验证全无人驾驶服务(2025年之前)之后,Waymo正将这一成熟模式加速复制至洛杉矶、奥斯汀等人口更密集、路况更复杂的新市场。
进入2025年底,其扩张步伐明显加快。
根据公布的2026年路线图,Waymo还计划进一步进入拉斯维加斯、底特律、圣迭戈、迈阿密及华盛顿特区等多个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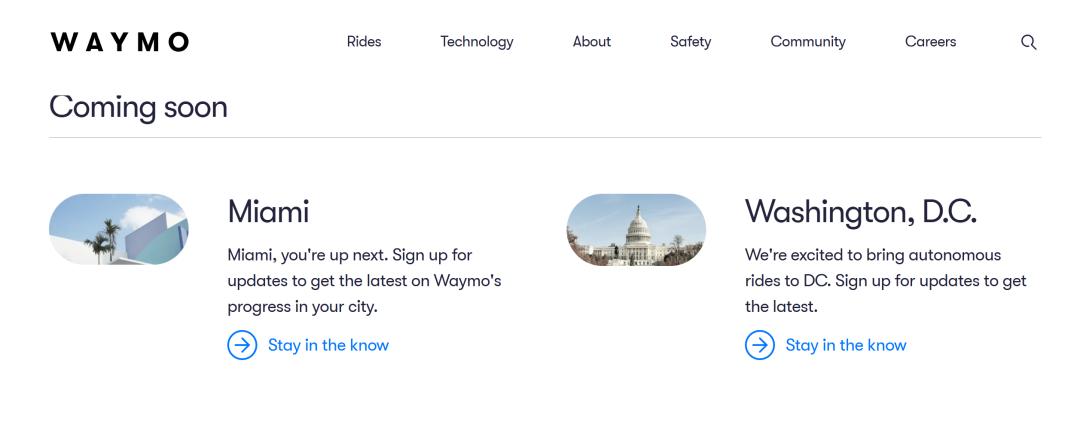
Waymo 即将进入的城市,图片来源:Waymo官网
可见,头部玩家的战略重心已从“技术可行性验证”阶段,转向了“可复制的商业化扩张”阶段。
在中国,以武汉、广州为代表的多个城市,已批准头部企业(如百度、小马智行、文远知行)的“全车无人”商业化运营。
可见,Robotaxi在国内也正加速变为一个需要面对真实乘客、产生真实收入、核算运营成本的B2C服务业态。
所有事实都指向同一个判断:行业正处在规模化应用爆发的前夕。
近期,小马智行(Pony.ai)副总裁张宁在采访中谈到,其第七代 Robotaxi 在设计之初,目标就已不再是技术验证,而是明确要“从运营角度上能够实现自负盈亏”。
这种从“技术闭环”向“商业闭环”的战略转向,是行业进入成熟期的关键信号。
而2025年11月6日特斯拉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则为此趋势提供了最强烈的呼应:
它明确地将CEO的未来十年薪酬,与“实现100万辆Robotaxi投入商业化运营”这一具体目标牢牢绑定。
“AI司机”被正式写入全球市值最高车企的财报目标和CEO的核心考核(KPI)中,成为一个必须按期交付的工程。
而这个“战场”,由中美“双引擎”共同驱动。
中美“双引擎”的竞逐
在太平洋两岸,这场竞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
美国阵营,巩固先发优势与路线探索
美国正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是以技术先驱为代表,在特定区域内深度验证高冗余、高安全性的商业模式;
二是试图通过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如纯视觉)和庞大的车队基础,探索低成本、广覆盖的规模化可能。
这两种路径的选择,背后是关于成本、安全与规模化速度的“哲学分歧”。
Waymo作为技术先行者,正努力将其十余年积累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深厚的商业护城河。
其周订单量已稳定在较高水平,与优步(Uber)的合作则显示了其开放姿态,意在将其顶尖的“AI驾驶服务”接入最大的“出行需求入口”,验证技术方案与平台流量的协同可能性。
特斯拉的探索性战略正进入实测阶段。
其在奥斯汀启动的试点服务,代表了另一种愿景:试图以纯视觉、低成本的路线,通过其庞大车队收集的数据进行“影子模式”训练,实现规模化泛化能力。
其目标是为行业提供一个不同于高成本、高冗余传感器的、更易于规模化部署的解决方案。

特斯拉Robotaxi车内情况,图片来源:特斯拉官网
中国阵营,集群式突破与生态整合
中国则展现出“多点开花、快速迭代”的鲜明特点。
头部玩家正积极推动大规模的无人化车队在复杂城市场景中的商业化试运营。
与此同时,一种更务实的“生态联盟”模式正成为主流:“科技公司+出行平台+主机厂”的跨界合作,旨在分摊高昂的研发与制造成本,共同加速生态的整合与落地。
百度萝卜快跑凭借其在多个城市的深入布局,在全无人化订单量上处于行业前列,正坚决地推动商业化闭环进程。
高德平台型企业的入局,则从需求侧重塑了竞争格局。它们将竞争从单一的技术维度,推向流量、地图、数据与运营能力的全面整合。
小鹏汽车、广汽与滴滴的合作代表着“AI能力”与“制造能力”和“运营能力”从早期就开始深度绑定,共同加速为Robotaxi设计的L4定制车型的量产与投放。
与此同时,无论中美,市场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头部集中。
技术浪潮与核心玩家
Robotaxi的起点,是技术人员对未来交通形态的愿景。
2009年谷歌自动驾驶项目(后来的 Waymo)启动时,目标是打造能应对多数人类驾驶场景的“AI司机”,这奠定了其技术探索的基因。
而真正推动竞赛加速的,是2016年前后资本的大量涌入,使行业进入了高投入的竞争阶段。
资本的注入推动技术从L3向L4探索,并逐渐形成了四种关键的玩家路径:
2.1 科技/AI驱动派 (Waymo / 百度Apollo等)
此类玩家的核心资产在于其软件算法(IP)与数据飞轮。
它们的路径特点是通过高成本、高冗余的传感器配置(如多激光雷达、高清地图)来追求极致的安全与可靠性。
这种模式的运营依赖持续的资本投入,以支撑庞大的研发团队和昂贵的硬件迭代:它们必须“烧钱”换取数据、时间和运营经验,直到运营效率和政策开放程度达到某个TCO(总拥有成本)临界点,才能实现商业模式闭环。
因此,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实现规模化盈利前,必须严格管理高昂的研发与硬件成本,并确保有持续的资金支持,以穿越可能到来的“资本寒冬”。
2.2 制造/OEM联盟派 (Cruise-通用 / Zoox-亚马逊 / 滴滴-广汽等)
此类玩家的核心资产在于其强大的制造能力与深厚的供应链管理深度。
它们背靠强大的工业资本(如车企、电商巨头),优势在于能从零开始定制化设计车辆,并在硬件成本控制上具备天然优势。
中国的滴滴与广汽的合作也属此类,旨在结合出行平台的庞大需求与车辆制造的工程能力。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CEO玛丽·博拉(Mary Barra)曾明确指出,自动驾驶的规模化是“一场资本和技术的马拉松”,这精准概括了联盟派玩家的耐力优势。
但此类路径面临的挑战是易受制于“联盟税”,即联盟内多方股东(如车企与科技公司)的利益冲突与决策内耗。
同时,重资产模式对市场容错率要求极高,任何重大的监管挫折(如Cruise在旧金山的事故)都可能导致运营全面暂停,风险敞口巨大。
2.3 全栈垂直整合派 (Tesla FSD / 小鹏汽车等)
此类玩家的核心资产在于其覆盖“AI-硬件-制造-销售”全链条的垂直整合能力。
它们的战略逻辑是:通过对软件、硬件和制造流程的绝对控制,实现最快的迭代速度和最优的成本结构。
特斯拉是这一路线的长期代表,其坚定地押注纯视觉方案。
而一个关键的行业动向是,小鹏汽车近期也进行了明确的战略转向,宣布将从过去的多传感器(含激光雷达)融合路线,转而优先发展纯视觉方案。
这种向纯视觉的“趋同”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信号。它标志着两家公司都将赌注押在了“AI的泛化能力最终可以取代昂贵的硬件冗余”这一判断上。
这也意味着它们面临着共同且放大的挑战:这种“全栈自研”模式需要极高昂的前期投入(研发、产线、数据)。
一旦这条纯视觉路线在解决长尾安全问题上的表现不达预期,其赖以支撑高估值的整个商业逻辑将难以闭环,高昂的沉没成本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和市场冲击。
2.4 平台/需求掌控派 (Uber / 滴滴 / 高德等)
此类玩家的核心资产在于其庞大的存量用户流量与成熟的需求聚合能力。
它们的路径特点是战略上侧重于MaaS(出行即服务)的市场入口,扮演“连接者”的角色,连接技术供应商与海量用户。
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其战略价值高度依赖于上游技术供应商的成熟度和开放性。
在产业链中,如果技术方(如Waymo或Tesla)选择自建运营闭环,平台方的核心利润就可能受制于上游技术方的议价能力,需要极力避免沦为纯粹的渠道商。
这四类玩家各自携带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结构性风险。
这种由不同基因决定的竞争结构,已预示了未来产业的高度集中化:数据飞轮、资本壁垒和政策门槛将快速提高行业门槛。
正如小马智行CTO楼天城所判断:“国内最终只会剩下3家左右的公司能跨越1000台Robotaxi规模化门槛。”
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市场现象的佐证。自动驾驶行业已经历了从“百花齐放”到“巨头收缩”的残酷洗牌期。
在美国,即便是背靠福特和大众两大巨头的Argo AI也因资金压力而被迫关闭;Uber和Lyft也先后出售了各自的自动驾驶研发部门。


国外相关新闻报道,图片来源:TechCrunch
这一系列“巨头退场”的事件清晰地表明,Robotaxi不是一个可以“顺带”完成的副业,它需要专注的、百亿乃至千亿级别的持续投入,迫使玩家将这场“烧钱”的游戏交还给资本更雄厚、战略更坚决的玩家。
在中国,行业同样经历了快速的优胜劣汰,大量初创公司因无法获得持续的“弹药”而在C轮或D轮融资后倒下或被并购。
资源和顶尖人才迅速向百度、小马智行等少数头部企业,以及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主机厂(如小鹏、华为系)集中。
中美两国共同的趋势表明,Robotaxi是一场“资本与技术的马拉松”,缺乏雄厚资本支持、清晰商业化路径或强大生态(如主机厂、出行平台)的玩家,正被加速淘汰。
走向终局的“壁垒”
当技术不再是唯一的瓶颈,行业开始直面商业化的真正挑战。
要实现万亿级的估值,Robotaxi必须从“技术验证”转向“商业运营”,并跨越三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性壁垒:
即“路权(能不能跑)”“经济性(赚不赚钱)”和“服务(好不好用)”。
这三大挑战,共同决定了谁能最终在终局中胜出。
3.1 路权突围:监管的“扳机”
Robotaxi走向规模盈利的根本前提,是监管对“路权”的实质性放行。
这不仅指移除安全员,实现真正的无人化运营,还需要足够大的开放区域(而非几个示范区)来确保服务需求密度,以及足够高的车队投放量来降低车辆和运营的边际成本。
因此,路权开放的三个维度——去人化、区域纵深和车队密度——共同构成了TCO(总拥有成本)曲线能否低于人力成本曲线的决定性要素。
Robotaxi的经济优势在于消除了占传统网约车运营成本60%以上的人力成本。
然而当前,政策的谨慎和公众信任是主要障碍:一次极端事故,就可能让行业数年的努力倒退。
正如Cruise的联合创始人凯尔·沃格特(Kyle Vogt)在经历重大事故后所揭示的:“技术上的‘万无一失’固然重要,但建立公众和监管的‘持久信任’是更难的工程。”
行业的突围,要求企业不仅提供技术证明,更要提供配套的解决方案:
包括构建高效的远程协助能力(Teleoperation),重构清晰的事故责任认定模型,并与监管方建立“渐进式、高透明度”的数据协同机制。
3.2 经济性突围:TCO的交叉点
路权解决了“能不能运营”的问题,而经济性则决定了“能否持续盈利”。
Robotaxi的底层逻辑是围绕“总拥有成本(TCO)的交叉点”展开的——即实现Robotaxi的TCO低于人力司机的综合成本。
这是一个需要精细计算的经济模型,而非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以深度TCO模型分析著称的方舟投资(Ark Invest)创始人凯西·伍德(Cathie Wood)认为:“Robotaxi的TCO每降低10%,其潜在市场规模就会扩大一个数量级。成本曲线的下降速度,就是这场竞赛的唯一时钟。”
行业正围绕这一临界点展开两种核心战略:
高固定成本路线(Waymo/百度Apollo等):
它们搭载昂贵的传感器套件,押注于通过极致提升车辆的运营利用率(例如,让车辆每天运行20小时以上),依靠在已开放区域加速“去人化”来摊薄高额的硬件成本,优先实现局部市场的TCO打平,进而实现盈利。
低固定成本路线(Tesla/Momenta等):
它们试图通过极致的硬件降本(如使用消费级摄像头)和数据的规模化泛化,从根本上拉低TCO曲线。它们押注于通过海量的车队规模(可能包含部分C端车辆),即便在利用率(日均运营时长)不及前者的情况下,也能率先实现TCO交叉点的到来。
无论如何,所有战略的终局都需指向经济临界点的实现。
3.3 服务与运营突围:MaaS的体验
Robotaxi的终极形态是MaaS(出行即服务)。
在跨越技术与路权门槛后,核心竞争将转向“好不好”的服务与运营效率。
届时,技术不再是唯一的壁垒,服务体验将成为留住用户的关键。
决定用户粘性和盈利能力的,是能否提供比传统网约车更高效、更可靠、更易用的服务体验。
要实现从技术L4到商业MaaS的转化,核心玩家必须在三个维度实现运营突围:
服务即时性:
这其实与“路权”的开放度相关,足够的车队规模和智能的调度算法,以确保用户在高峰时段也能被快速响应,减少等待焦虑。
无人化后勤:
这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巨大挑战。必须建立闭环的、低成本的无人化充电、维保、清洁和夜间泊车体系。否则,高昂的“后勤人力成本”将吞噬“去人化”带来的经济优势。
用户体验:
建立高效的协同应急机制(如应对乘客遗留物品、车辆突发故障),并设计更人性化的AI交互界面(如流畅的语音沟通、清晰的路线规划),以弥补因无人化而缺失的服务“温度”。
Waymo在2025年下半年的运营动作,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焦点转移。
2025年9月,Waymo宣布与Lyft达成重要合作,共同在纳什维尔(Nashville)推出Robotaxi服务。
此项合作的关键,在于清晰的“分工”:
Waymo提供核心的“AI司机”技术,而Lyft则利用其Flexdrive平台,负责构建和运营一个专为自动驾驶车队服务的“运营管理设施”,其核心职责正是解决充电、维保、清洁以及支持客户服务(如遗失物品寻找)等一系列复杂的后勤问题。
Lyft的CEO David Risher在谈及此次合作时,将其描述为“一流的自动驾驶技术”与“一流的客户服务和世界级的车队管理能力”的结合。
在中国,这一运营挑战也得到了来自出行平台的印证。
广汽集团旗下的出行平台如祺出行(Ruqi Mobility),作为连接主机厂与出行市场的关键玩家,其CEO蒋华(Jiang Hua)在2025年的行业讨论中,也多次指出了“无人化后勤”是规模化的真正瓶颈。
他强调,Robotaxi的运营绝不仅是AI驾驶,而是包括车辆的整备、清洁、维保、充电,以及如何高效处理客户遗失物品等一系列极其琐碎的“服务运营”难题。
蒋华认为,这正是出行平台的“主场”优势。
与纯技术公司需要从零开始构建庞大的后勤团队不同,一个成熟的出行平台(如如祺)已经拥有了服务数万名人类司机的线下运营网络和经验。这种能力可以被“复用”于Robotaxi车队,从而在解决这些“脏活累活”上,实现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运营效率。
这一系列联盟与战略布局标志着头部玩家已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规模化的MaaS,仅靠“AI驾驶”远不足够,必须解决背后庞大且琐碎的“无人化后勤”与“混合运力管理”的挑战。
Robotaxi的成功,最终将是政策路权、经济TCO、运营MaaS三者效率的乘积,缺一不可。
价值的重估
市场对Robotaxi的估值,并非基于传统的线性增长预测(如“卖出更多出租车服务”),而是基于对其价值的非线性增长预期。
一旦一家公司证明了其商业模型TCO < 人C的可复制性,其价值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市场重新评估。
因为这证明的不仅是一种新服务,更是一个全新的“城市交通操作系统”的诞生,其验证的是未来全球交通网络的巨大潜力。
正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师团队所指出:“Robotaxi的规模化将是本世纪最大的资产类别重新分配。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出行本身,对全球汽车制造、能源、城市商业地产以及保险业产生数万亿美元的结构性重塑。”
硅谷著名投资人、Greylock Partners合伙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也对此补充道:“Robotaxi不仅仅是‘更好的出租车’,它是一个全新的平台。真正的大赢家,是那些能利用这个平台构建次级生态(如车载商业、即时物流、数据服务)的公司。”
竞赛已进入中后期,资本的窗口期正在缩短。
这是一场高度依赖规模与效率的竞赛:资源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少数头部玩家集中。如果不能在格局固化前获得足够的用户和数据,企业将很难获得后续资金支持,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而那些在AI算法、资本效率和运营管理上实现有效整合的少数企业,将可能拥有核心资产与长期回报,成为这场出行变革的主要参与者。



